允應Gary﹐胡謅些什麼﹒ 提筆﹐回首顧盼﹐着實平淡﹐乏善可陳﹒頃讀一存兄E簡﹐ 一首熟悉又 近乎遺忘五十年的歌"濃密密的烏雲堆滿山頂·······"由心底泛起﹒燕紛飛﹐雁過了﹐可曾記得留下的聲音?
時序回到近六十年前﹐我開始長大,有了記憶:
天剛亮﹐寂靜的大院子裡﹐總能聽到"大餅、饅頭、豆沙包"
一聲聲帶有山東口音﹐疲憊沙啞的叫賣聲﹐ 由遠而近﹐騎著腳踏車﹐足蹬黑布鞋﹐身着舊汗衫﹐ 脖子上總是圍着一條毛巾的大叔﹐後座置一長方形的木箱﹐打開箱子掀開覆着的厚棉布﹐ 冬天時猶能見到冒出箱子的熱氣及白煙﹐有大餅、白饅頭、三角形的菜包及長形的豆沙包﹒ 這沙啞的聲音﹐伴著我成長﹒
也不是經常﹐ 但總是在黃昏﹐巷口有騎著三輪板車﹐做爆米花的﹐ 幾乎是各家出米他出工﹐地上擺置一罐罐克寧奶粉的罐子(說到克寧奶粉的罐子﹐ 想起勞作老師方家鐸﹐ 教我們用罐子做的書架) 裝滿白米﹐排著隊、殷切的等那"轟"的一聲﹐(膽小的摀著耳朵﹐又害怕﹐又期待)﹐冒起一陣很香的白煙﹐將爆好的米粒倒在長形的鋼網裡﹐再倒在大鐵盆內﹐加上麥芽糖、生﹐ 攪拌後鋪於模板上﹐壓擠切塊﹐印象中都是置於金雞牌的餅乾桶內﹐予以保存﹒(唯至今想不透的是﹐那年頭沒有塑膠袋﹐怎麼拿回家的?) 那轟然的响聲﹐那帶香味的白烟﹐彷彿而今猶未驅散呢!
若是聽到 (一根小木棍﹐綁上一個小鐵罐﹐罐中有一如同鍾擺的鐵片﹐ 用手搖晃﹐發出一種鐺鐺聲)﹐ 那是賣麥芽糖的﹐ 除了一兩毛錢買一根 (用竹籤挑起﹐轉一兩圈﹐ 即一根帶著細絲,味美的麥芽糖) 也可以用舊鐵罐換糖,他的腳踏車前掛滿了收來的舊鐵罐﹐ 後架上懸掛兩桶長方形的鐵桶﹐掀開鐵蓋,有著晶瑩誘人的麥芽糖﹐ 記憶中我永遠是在一旁唾涎的那一位﹒
隔一段時間﹐能聽到:"賣竹篙、掃帚啊"用台語發音﹐ 聲音拉得很長﹐ (我到很久很久以後﹐ 才知到他說的是甚麼)也是三輪板車,車上有各類雜貨﹐ 我家後院的曬衣竹竿﹐ 夾煤球的鐵夾﹐ 劈柴的小斧頭﹐····等都是來自這活動的五金行﹒
總是在星期假日﹐一個帶有上海口音﹐ 重覆著兩句:"擦··皮··鞋··啦··""皮··鞋··擦··啦··" 他背著長方形﹐繫著帶子的木箱﹐將收到的皮鞋﹐整齊的排在跟前﹐或在樹荫下﹐ 或在屋簷下﹐ 坐在木箱上﹐ 專注的將皮鞋擦拭的光亮鑑人﹐ 他不多話﹐即使我們圍在一旁,也不多言,在完工後默默離開﹐継續"擦··皮··鞋··啦··"每每望著那寞落的背影﹐ 也會如他的腳步一般的沉重﹒
冬夜﹐常常聽到一種聲音﹐水壺中水燒開了﹐發出的"嗶··嗶"聲﹐那是賣麵茶的﹐很遺憾﹐自幼只聞嗶聲響﹐卻未曾嚐過﹒
也是在晚上,天很黑了﹐一聲聲"答··答··"輕脆打竹板的聲音﹐(用竹筒剖半﹐用竹板敲打)﹐聲音可傳到老遠﹐沒錯﹐是賣餛呑麵的﹒ 若能站在推車旁﹐望著湯鍋邊那泛黃油亮的竹筒片﹐聞著鍋內冒出香氣的白烟,吃上一小碗﹐那可是非常非常幸福的﹒
有些聲音﹐無所不在﹐也揮之不去﹐ 我很不喜歡﹒殺豬﹐豬的慘叫聲﹒ 我家前院前有一排宿舍的木圍籬﹐圍籬外有一小溪﹐小溪對面約300公尺是緊鄰96巷的一大片空地﹐亦常作曬榖場﹐每於深夜﹐聽到淒厲得叫聲﹐不曾﹐也不敢去看﹐即使趴在圍籬﹐由縫隙遠觀也不敢﹐ 那是所惡者其一﹒野台戲﹐經常於曬穀場空地搭起台子﹐ 不知是酬神還是別的﹐總是一搞大半個月﹐從下午到深夜﹐鑼鼓喧天﹐ 且不知唱些甚麼﹐及長方知是唱歌仔戲﹐ 此乃所惡者二﹒嗩吶聲﹐ 和平東路到底﹐三段﹐六張犁﹐ 有公墓﹒常見載運棺材一路吹嗩吶敲鑼鼓的車隊駛過﹐但那嗩吶聲再遠也聽得到﹐我雖小卻也知道這聲音即意味著還不甚明瞭的【死亡】﹐ 害怕父母死掉,這也是我所惡之最﹒
有些聲音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的﹒ 我家因緊臨小溪﹐每年總有一次﹐夜半溪水暴漲﹐溢過水面﹐順著小坡坎流入我家﹐流過竹籬笆﹐流過小花園﹐流過後院﹐流進後院巷子的小陰溝,溪水流得不是很急﹐但也能聽到淙淙水流聲﹐晨起﹐ 赤足踏水﹐清涼沁心﹐當此刻春水溢滿小院﹐春天到了﹒ 宿舍裡常有些另類的聲音﹐如爬上大樹﹐在高枝枒交叉處置放許多小石頭﹐ 風動、石落﹐有落石聲﹒如在許多童伴玩遊戲時﹐ 將樹叢中的蜜蜂窩用竹竿挑掉﹐我先跑﹐爾後就能聽到一遍哭聲﹒如宿舍大門口﹐ 門房老李在門口起個炭爐﹐我好心﹐ 沒有用大龍炮﹐用水鴛鴦﹐丟進
小爐裡﹐引來陣陣哀嚎聲﹐ 而前此種種﹐最終是換來老爸的怒罵聲!
夜深了﹐往事歷歷﹐聲猶在耳﹐ 望著漆黑的窗外﹐ 此時無聲勝有聲﹒
屠嶽

![waiters_waitress_clap_sing_birthday_song_lg_nwm[1] waiters_waitress_clap_sing_birthday_song_lg_nwm[1]](https://blogger.googleusercontent.com/img/b/R29vZ2xl/AVvXsEhLSGW5N8Y-xs-xw3Loh4sAtvJ3vIXAirSJvFXQUpIuzggq08zuoy3-cDa1hfotXdsu3p_Lk7XYmBs-8hMCbaPaYaQU0tUftxakWuSUZvaI3M9i_873g0Du7_6ThGm6Vgc5hBa0BMkiBnRy/?imgmax=800)


![ww2_medal_swing_lg_nwm[1] ww2_medal_swing_lg_nwm[1]](https://blogger.googleusercontent.com/img/b/R29vZ2xl/AVvXsEg1dKnYmT7BnLYS5y92c1Vm-e7fWqCF2ve2Niw0MXdLb6qHuHhVjCeHla7unlPgwJy3ZpWXLKDP7FGTvuYRxUL4eYTEgF4S4QXzeGXZ9SFzJFsMPPrTRCJleJRuPoObQjhBwRKEe_hRCB43/?imgmax=800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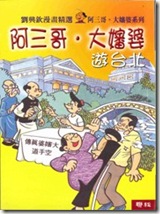

![ling_run_fly_kite_lg_nwm[1] ling_run_fly_kite_lg_nwm[1]](https://blogger.googleusercontent.com/img/b/R29vZ2xl/AVvXsEgBiArz9nC_kipsZ3rRVAkc5-8UAgbzvSIKSkLpq7wtBR7xaA9031UgsubvBKljhVY9jJbmPZjiS4MLFbrnqrHn10lKpMBeeRn5MWsaKyxiOaOHMe9LC95mooT6ctY8pjZ0252wD7cu1sKM/?imgmax=800)


![animation_white[1] animation_white[1]](https://blogger.googleusercontent.com/img/b/R29vZ2xl/AVvXsEjPYGpt_uJYgfcIuhtrm9h5qsUFKr7hKpbZz7HHUeOgUHN8yqHwUa7EO_D-r9XbZXkn0RABVZeD3i95K_qwfq3pYqZA4i1CZO_vsGosi9CSDYQu4qHSLoNEbC7pRF4FymxEg2Px9XJ0TJ9a/?imgmax=800)
